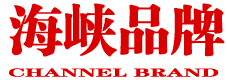“打赌”
——追忆在渭田中心小学的美好时光
危廷芳
少年学生时代是最美好的时光,总是能在脑海里留存很深且美好印记!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不时地回想起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闽北山区的校园生活,回想起少年时代的一次“打赌”。

我所在的松溪县渭田中心小学,是渭田公社十几二十个大队唯一的完小。大部分高年级(五、六年级)的学生都是寄宿生。因为除了公社所在地的渭田小学以外,其他大队的小学一般都只设一到四年级的班次,要继续升学就必须到渭田小学去寄宿。那时恰逢中国经济处于最困难的年月,为保民生,国民教育进行了必要的紧缩和调整。我们五年级的同学都经历了四年级到五年级的统一升学考试。在松溪县八个人民公社之首的渭田公社人口近万,但渭田小学五年级的学生数还不满 70 人,因校舍简陋,教室容量所限分成两个班。到了六年级,虽然饥饿对于普通人们的严重威胁已开始缓解,但是许多同学家里还是无力提供 1.5 元的学杂费,或家里缺少劳动力而退学,两个班就合并成不满 40 人的一个班。二、三十位寄宿的同学就拥挤在一间几十平方米上下两层大统铺的宿舍里。我们日常的吃饭休息睡觉嬉戏打闹都在这一小小的空间。

学校没有食堂,只有一间烧开水和蒸饭菜的厨房,只负责蒸老师的饭菜和学生的饭,为老师供应开水,不负责蒸学生的菜,也不为学生提供开水。学生渴了都是到校门口的渠沟里取冷水喝。好在当时民风十分淳朴。水源流经的几个大队的村民都早已约定俗成:在黄昏以后到第二天早晨 9点之前自觉自愿不到河里捣衣、洗马桶、洗尿桶。我们在渭田小学的二年学习时间里,没有听说有因喝生水闹肚子。老师蒸菜蒸饭的搪瓷缸放在一个诺大的蒸煮木桶的最上层,学生的放在下几层。那时还没有铝饭盒,学生的搪瓷缸有时哪怕放下的水很少,取出的可能也是满满的一搪瓷缸的稀饭。尤其是夏天的早晨,取出往往是泛黄的酸臭稀饭或糊饭,因为吹事员都是在晚上就把饭菜蒸熟、冷却、发酵了。我们小小年纪,哪敢与吹事员计较这一点点有利于老师的小事呢!况且,同学们家里都是省吃俭用供米给我们寄宿上学,肚子又经常处在半饥不饱的状态,再不好吃也总是争先恐后地取来排排坐在床沿边用周末回家取来的咸笋、酸菜佐餐,稀里糊涂地吃下肚子里,就赶忙去上早晚自习。
虽然条件艰苦,学校对学生的学习还是抓得很紧的。语文算术课任老师每天都要在上早晚自习期间坐在教室的讲坛上,一边监管着我们自习做作业,一边用红笔涂改订正我们的语文算术作业,并在下一节课的前十分钟进行讲评。我在 1979 年,凭借的就是在渭田小学的五六年级和后来上初中一二年级学得比较扎实的语文、数学基础,才能自学初三和高中课程,考了全县第二名的成绩,被厦门大学录取。

我们寄宿的同学,不要为家里的农事帮忙,除了上课和早晚自习,又无午休的习惯,每天还是有一些课余时间的。学校仅有几百平方米的小操场,连个半场的篮球架都没有,又无经过专门培训学习的体育老师,体育课总是“一、二、一”的队形训练或“丢手帕”“跳绳”等游戏。玩久了毫无兴趣可言。又没有任何的其他玩具,即使天才想象力的人也无可预知到现在孩子们的玩具是变着花样铺天盖地的堆满了一屋子。但再苦、再穷、再没有条件,也抵挡不住孩子们爱吵爱闹爱玩要开心的天性。
夏天,下课后总是迫不及待地到离学校三百米之遥的松溪县著名的“五福桥”下游泳消暑。

冬天,我们就拿着各自用杉木板制作的乒乓球拍,在一张未曾油漆的乒乓球桌上争“官”做。人多只能打四个球,输者下台,轮番进行,我曾是打遍几十个同学的擂主。想不到的是,1964 年在我升学到松溪中学(全县唯一一所中学)时,在一次全县少年乒乓球比赛中获得了第二名。这就如一个人在小腿上绑着一个沙袋练跑步,一旦卸下沙袋他便健步如飞。
雨天,我们就在教室里或宿舍的床铺上打“四十分”、 “争上游”,谈笑和争论声总是盖过外面的下雨声。

下晚自习后,几十个同学各自捧着一个煤油灯如龙游般鱼贯而入回到宿舍。有的同学马上用煤油灯照明又开始午间尚未决出胜负的“四十分”而战斗;有的则在床铺上叠罗汉、翻筋斗等杂技表演;有的溜出校门到渭田街唯一的一家“地下”(那时是不允许做生意的)包子铺用家里给的定时定量的大米去兑换包子吃。一般是一竹管(那时闽北山区都是用毛竹做成大小不等的量米器)六小两米(就是现在的 3.75 两)换一个包子。下晚自习后的半小时,是我们寄宿同学最自由、最热闹、最无约束、放松放荡的时候,争论声、吵闹声总是令楼上的老师无法备课和休息。每天的值班老师总是准时地来到我们的宿舍门口,猛然吹几声哨子。刚才还如沸腾了的校园,瞬间安静得如无人之地,唯有一墙之隔的沿着通往“五福桥”的鹅卵石路边的供渭田街百姓也供我们学校日常用水的沟渠的潺潺流水声。

当然,有些年龄稍大的同学也忘不了在深夜摸黑“欺凌”小同学搞恶作剧。最经常的就是把熟睡的同学嘴边用钢笔画几根猫须,或在脸上对称地画上几朵花。有一个晚上,我边上的一个同学睡得很香,我们睡在他边上的几位同学便拉下他的裤子,看他蜷曲着身体,就用一根小红绳一边绑着他的脚拇趾,一边绑在他的“小弟弟”上,满以为有好玩好戏看。第二天早晨,当他睡眼惺忪地坐起时,我们边上的几个同学也立刻反转身坐起,盯着他萌萌的样子在呵呵的笑。他开始并不知道我们笑什么,也跟着我们傻笑。当他掀开被子,才发现自己光着下身,一根小红绳系在他的脚拇趾,另一头则早已松开了“小弟弟”,其他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我们怎么会忘了那“小弟弟”是有极强的伸缩性的啊!怎么能绑得住呢!于是,我们一起开怀大笑,一会儿全宿舍的同学都围拢过来一起捧腹开心的大笑。
遥想当年,我们都是来自流经渭田公社的一条河边的相隔一、二公里的四个大队的同班同学。星期六下午(那时星期六上午还是上课的)我们便一路说说笑笑、打打闹闹溯洄到各自的家,享用母亲念孩子一个星期咸菜、糊饭的不易而特地准备了香喷喷的白米饭加韭菜炒鸡蛋。星期天的下午,河源头的同学最先出发背着咸菜和米溯游召唤其他同学又一起回到了渭田小学。如今,这些搞恶作剧的同学都早已退休赋闲,有一个同学已经离世。我现在想起那个好玩好笑的早晨,想起少年时代的美好时光,便会情不自禁地思念他们,由衷的感谢他们少年时期的陪伴和照顾。

一天晚上,老师们都被通知去公社开会(改革开放前,所有的老师都是干部身份),我们没有了老师监管,早早就下晚自习回到宿舍重复往日的游戏。久了累了,同学们的“饿饿虫”都爬到喉咙管,未免又想起渭田街的那个包子铺。有的说,我能吃六个,有的说,我能吞下八个……热闹场面胜过现在“公开招投标”的开标场面。其中年龄最大个子也较壮实但人很实在的同学(他姓叶,我们平时称他大叶),居然说他能吃下十三个。他说出这个数字后,大家都愕然了,再就没有人敢说能吃下更多的包子。
“你真能吃下十三个么?”我们宿舍中那位最爱搞笑,威望最高的同学首先站出来与其抬杠。凡是有人群的地方,总是自然而然的会有“领头人”。这样自发产生的“领头人”一般都身材比较高大,好打不平,还有一些笼络同学的小“伎俩”。如还能学习好,聪明的班主任就会发动大家把他选为班长,使之成为并轨的“领头人”。
“能!”大叶不假思索,毫不示弱地说。
“好吧!那我们与你打赌。我们凑米去换回十三个包子你能全吃下,那就白吃;你如果吃不下,那就返还我们十三管米!赌不?”“领头人”这么一说,其他同学一呼百应,都愿意出米凑这个赌注。

大叶起初认为大家只是画饼充饥、说说而已,没想到现在竟然要来真的,未免有些退缩。如果吃不完十三个包子,要返还十三管米,那是家里给的一个星期的伙食米啊。但海口已经夸下,怎么好在这么多同学眼前当众示弱成为一个孬种沦为大家的笑柄呢!那是一个“学雷锋争做好事”又十分崇尚战斗英雄,视信誉很重要的年代。再说那包子的诱惑力,早已使他垂涎欲滴。于是,他顾不了那么多,脱口而出:“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同意与大家打这个赌!”
不到半个小时,我们就凑齐十三管米(四斤半多一点)从不到一华里路外的包子铺换回了热气腾腾的十三个一搪瓷盆的包子,置放在大统铺上层的中央。大叶圈腿坐在搪瓷盆边,目光注视着即渴望又生畏的十三个包子,好像就要开始一场残酷的战斗,不自觉的卷起两边的袖口;凑赌注的同学围着大叶和那盆包子坐在里圈,这是他们凑米而获取的一点更为直观的位置优势;外边则是因缺米而未凑赌注的其他同学。就好像平日里在渭田街头偶遇到来自安徽、河南灾区的乞讨人员耍猴子一样,二三十双眼睛都盯住大叶和那一盆包子,嘻笑争论着“大叶是否能吃下这十三个包子”,急切地等待这台好戏的非此即彼的结果。
在那闪着微弱泛黄的煤油灯光下,大叶抓起一个滚圆的包子,一大口下去,就成 U 字型,再一口就变成 L 型,接着将 L 往嘴里塞去 ,片刻功夫就消失了一个包子。他毫不费力的吞下五个包子后,还略微抬起头,对着我们笑,似乎他今晚稳操胜券。
但大叶此后依次每吃一个包子都要比前一个来得慢一些。这就如经济学上的“边际递减效应”,同一享受的不断重复,则带来的享受逐渐递减。随着他吃下的包子越来越多,其获得的享受和快乐则越来越少。当他开始吃第十个包子时,明显感到吞咽得更加缓慢。如果说大叶吃第一个包子是极大的享受和快乐,那么,他吃的这第十个包子就毫无享受和快乐可言,等于零享受零快乐。更何况还有三个令他有些恐惧的包子,不仅不是享受和快乐的递减,而将是痛苦与难受的递增!
这时,我们宿舍的“领头人”又首先劝大叶说:“别再吃这三个包子了,我们也不要你返还那十三管米!”按现在的话说叫停止“零和博弈”,不分胜负。并且,他还征得坐在内圈凑赌注同学的同意。他想作这样的妥协,是担心大叶会吃出问题来。但是,出乎大家的意料,大叶居然还要把这“游戏”继续下去。他要信守自己的诺言,输就是输,赢就是赢。但他提了一个要求,给他取一杯水来。很快一个同学就到校门口的沟渠里取了一搪瓷缸的生水放置在大叶的眼前。
经过大致十几二十分钟的折腾,一切又恢复到开始的场面。所不同的是,大叶再也不能像开始时那样利索地快乐地享受地吃包子,而是像漂浮在池塘上的大白鹅已吃饱了嫩草后又逮住一条小鲤鱼尽力地伸长着脖子硬生生的往下吞一样,大叶也总是把包子一小块一小块地掰着送到嘴里,呷一口水,细咀慢嚼,然后抬着头伸长脖子硬生生的一口一口往下慢慢咽。此时不喝水,难以下咽;喝了水,如海绵般的肚子又膨胀得厉害。明显看得出,越往后面,他越力不从心,豆大汗珠如注般地从额头上往外冒。当他咽下最后一口时,四肢朝上,急不可待地就躺了下来,突出滚圆的大肚子。其惨状又如一个醉汉瘫倒在地的“现场直播”。所不同的是,大叶咽下的包子怎么也呕吐不出来,并且痛苦地呻吟着。
怎么办?大家面面相觑,有些慌张。最后,目光又都注视着那位“领头人”,急切地等待着他拿主意。
此时,“领头人”俨然是战地的指挥员。他稍稍皱了皱眉头,迅速地叫几位同学留在上铺腾挪大叶,其余同学马上下地接举,另外几个同学到校门口架起双轮板车(学校师生每学期两次上山砍柴火用),沿着鹅卵石铺就的路面,十几个同学拉的拉,推的推,不一会就把大叶拉到公社卫生院。冲在前面的同学早已敲开了卫生院的大门。院长了解情况后,神情十分严肃地说: “你们搞的什么鬼!这是会死人的!”随后叫醒了几乎全院的医护人员。那时候没有引流、洗胃、灌肠的设备,全凭借他们的推拿和引流的药物,忙乎了几个小时,才逐渐让大叶吞咽的面包呕吐出来。
当我们掏出角分的零钱凑足缴纳了大叶的医疗费用时,东方已露出鱼肚白——天已破晓。由于一夜的兴奋惊慌,我们早已忘了饥饿而这时也没有了饥饿感。我们一句话也没有说,默默地拖着沉重的步子用疲惫的双手推着躺着大叶的双轮车往学校方向走去。仿佛一夜之间我们心照不宣地体悟到什么……知晓了什么……
这是尘封了六十年前的事了。
人总是倾向于为那些曾经经历过的事建立起纪念碑,让这些记忆在情感的深处重新焕发生机,获得新的意义。在我们的少年时代,缺的是衣食住行的物质,不缺的是艰苦朴素、独立自律、苦中作乐、团结协作、勇敢担当、共克艰难的精神。然而,在我们国家经济社会翻天覆地变化,人们生活富裕美好的今天,青少年们所缺少的正是一甲子前的青少年们所不缺的精神,而不缺的又正是上世纪 60 年代衣食住行样样都缺的物质。在这大发展大变革的时代,穷怕了的人们在对科学技术对物质的奋力追求的同时,难免有些人忽视对精神方面的跟进,有的人甚至曲解了“富裕是文明的前提”,以为科学技术和经济搞上去文明就自然成,忽视了对青少年的传统道德品质教育和德、智、体的全面发展。在一些青少年中,远大的理想变成纯粹的“个人奋斗”。时至今日,有些地方和学校还是唯考分为指挥棒,虽然有些人从小就开始起早睡少地进入激烈的考分竞争的斗志磨练,并把不一定对科技创新有最佳功效的考分逼上去,但同时也在一些青少年中逐渐形成狭隘自私的畸形人格,缺乏集体主义精神和大局观念;对艰苦朴素的教育更是嗤之以鼻、不屑一顾,代之的是贪求奢华、比吃穿比爹娘。有的在“阶级固化”的论调误导下,“个人奋斗”也无补于事,精神颓废,干脆躺平不干。这就造成了一些青少年在价值观方面的问题,甚至在少数青少年中出现霸凌伤害同学的事件。在这样的时候,有的地方和学校总是忙乎一阵子,出台补救措施。但我们更不应该忘了,要坚定不移地按照党中央的要求,继续通过“刨根究底”的教育制度改革,更加全面地创新适应新时代的青少年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形式、教育内容、教育方法。对历史最好的继承,是创造新的历史,让我们的教育再次建立起更加璀璨的纪念碑吧!